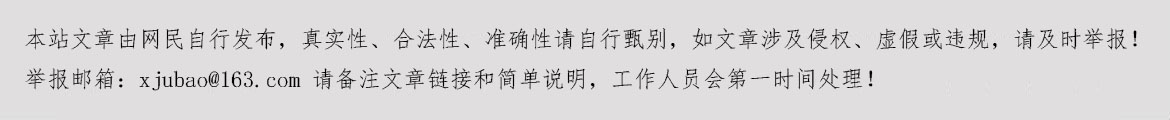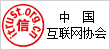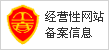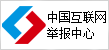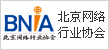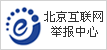捐光3000万,女神不是富婆
2023-04-21 11:00:00
遵仁台 https://www.zunrentai.com/
叶嘉莹,是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先生,她一生大多数时候,是无处可逃的,是诗词让她在绝境中安身立命。
她,是个苦命的人。
父亲因战争流离失踪,母亲因病早逝,这种痛苦在少女时期,就在叶嘉莹的内心日夜发酵。
九十多岁的叶嘉莹,总是身穿一件烟紫色的长衫出现在讲台上,尽管自己腰腿患病,她还是拒绝了柔软舒适的靠背椅子,坚持要站着讲课。
她满头银发梳得整齐,双目炯炯有神,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,中气十足,从声音到体态,不由得让人发出一句慨叹:“真美啊。”
旁人很难从她的这份平静中,看见过去时代的汹涌往事。
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,成为她一生的写照。
从漂泊到归来,尽管活在这世上有过各种创伤,叶嘉莹还是在艰涩的生活、远方的诗词里寻得力量,体面地活着。
叶嘉莹的生活清苦,打开冰箱,里面只有几把略发黄的蔬菜与半瓶豆腐乳,在青菜汤的淡味里,她觉出了一生凄凉。
叶嘉莹,是在北平四合院出生的,因来到这世界时是荷花遍布的夏天,父母就为其取小名为“小荷子”。
在书香门第的大家族里,她的祖父是光绪二十年的进士,叶嘉莹家的大门处有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,上面写着“进士第”,门前还有两只石头狮子。
在她儿时的记忆中,家里有大堆的书,都是父亲从祖父那继承过来的。
这些书陪伴她,走过了少年时代。
小时候的叶嘉莹,很少出门,她跟着祖父在家中读诗作诗,读的最熟的是《论语》,她说:“我可以一天不吃饭,但不能一日不读诗。”
叶嘉莹(中)小舅李棪(左)弟弟叶嘉谋(右)
后来,她的别号“迦陵”也是从童年时期与祖父聊诗词中得来——清朝的陈维崧,是中国词人里写得最多的,号迦陵。
十三岁之前的叶嘉莹,过着人生为数不多的轻快日子,她对着院子里的树木、月光、落叶作诗,她是在家里由身为教师的姨妈授课。
她爱上了中国古典文学与诗词,在13岁就写下这样的诗句:
“几度惊飞欲起难,晚风翻怯舞衣单。
三秋一觉庄生梦,满地新霜月乍寒。”
才华开始在叶嘉莹的身上显露,这已经注定她不平凡一生的开始。
青年时期的叶嘉莹
1937年7月7日,在北平郊外卢沟桥,日本军队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。
兵员伤亡数百万,千万百姓逃亡内地,老弱转于沟壑,壮者疲于奔命。
日本人进城是从前门堂而皇之进来的,彼时的叶嘉莹在读初二,这年暑假“七七事变”,她无比清楚地听到了卢沟桥响起炮火的声音。
这年,叶嘉莹才13岁,北平沦陷。
13岁的叶嘉莹
她所居住的西长安街,时常会见到日本人的军车呼啸而过,他们在车上唱歌,唱《支那之夜》。
在这样的情境下,十三岁的叶嘉莹写下诗句:“尽夜狂风撼大城,悲笳哀角不堪听。”
在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中,叶嘉莹回忆,当年的风雪比现在大,冬天出门上学,她走到巷口拐弯的地方,就会在街上看见冻死、饿死的人。
战乱中,长期在上海工作的的父亲断了消息,生死未卜。
母亲长久地挂念丈夫,愁思让她得了重病,需要去天津租界找医生治病,可是在手术过程中感染了,不幸在回北平的火车上猝然离世。
叶嘉莹戴孝照
那是叶嘉莹最痛苦的时刻,她清楚地记得,母亲棺殓时钉子钉在棺木上的那种声音,她知道悲与喜的差别,也懂了生与死之间的距离。
母亲去世那年,叶嘉莹只有18岁,她很后悔,当初没有陪母亲去天津。
“噩耗传来心乍惊,泪枯无语暗吞声。早知一别成千古,悔不当初伴母行。”
山河破碎风飘絮,身世浮沉雨打萍。失去了母亲的庇护,叶嘉莹开始直面战火纷飞的世界。
叶嘉莹与两个弟弟
1941年,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,专攻古典文学专业。
叶嘉莹平常在学校里很少与人讲话,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图书馆或者教室,安静地看书。
她在辅仁大学读书时,受老师顾随熏陶很大,每次上课都用心记录,希望能把先生所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载下来,两人常在一起讨论古诗词。
那八本笔记,跟随叶嘉莹漂泊了很多地方,她的财物都可以不要,也要保留好顾随先生的思想。
叶嘉莹(右二)与顾随先生及同学合影
叶嘉莹称顾随先生带给她的,是心灵的启发,顾随也对这位学生很是认同,他在看完叶嘉莹的诗词习作后说“作诗是诗,填词是词,简直是天才”。
在艰辛的生存环境下,叶嘉莹创作了大量的诗词,她对诗歌有很敏锐的感受。
“日月等双箭,生涯未可知。
甘为夸父死,敢笑鲁阳痴。
眼底空花梦,天边残照词。
前溪有流水,说与定相思。”
叶嘉莹大学毕业照片
在动荡不安的日日夜夜里,叶嘉莹不知道沦陷的祖国何时能回来,也不知道杳无音信多年的父亲何时能回来。
叶嘉莹用诗词自渡,等到父亲回来的那一天,叶嘉莹已经大学毕业了,在学校里教书。
那天,她正把自己的自行车抬出去的时候,就看到门前一个熟悉的身影,叶嘉莹仔细一看,是自己阔别已久的父亲。
当年,父亲离家的时候,她还在读小学,彼时的她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,父女二人相拥泪下,他们都吃了太多别离与生活的苦。
叶嘉莹与父亲
叶嘉莹说自己一生没有谈过恋爱,结婚也不是因为爱情。
秀外慧中的叶嘉莹,经常被各大学校邀请前往讲课,有次她遇到了自己中学的老师,彼时的她并不知道,自己即将开启一段悲剧的婚姻。
这位中学老师将自己的堂弟赵钟荪,介绍给了叶嘉莹。
很快,两人见面了,赵钟荪对叶嘉莹一见钟情,聚会结束后,他坚持要骑车送叶嘉莹回家。
叶嘉莹的父亲不喜欢这个男孩,因为觉得他学无专长。
学无专长,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就立不住,后来所发生的一切,证明了父亲的判断。
1948年,21岁的叶嘉莹南下到上海嫁给了赵钟荪,之后跟随丈夫到了中国台湾。
叶嘉莹随身携带的行李特别简单,只有两个皮箱,里面装着顾随老师写给她的笔记,还有几件换洗衣服,她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时,没有想到这一别就几十年都不能回来。
叶嘉莹开始了漂泊的生活,她惨遭迫害,随命运拨弄和抛置。
在生大女儿时,赵钟荪将妻子放到海军医院的走廊,自己就离开了,叶嘉莹独自一人从天蒙蒙亮坐到了天黑,羊水都流光了。
赵钟荪的姐姐赶到,借了一辆吉普车,将叶嘉莹送到了高雄的医院,医生给她打了催生针。
叶嘉莹从晚上九点钟一直痛到了第二天下午才生产,后来,回忆起这段难产的经历,她还是面露痛楚:“把我痛得真是要死了!”
没多久,丈夫就因“白色恐怖”入狱4年,叶嘉莹也险些被捕,她带着襁褓婴儿被带到警备司令部问话,警察局局长见她可怜,就把她放出来了。
“时外子既仍在狱中,余已无家可归,大地茫茫,竟不知托身何所,剩抚怀中女,深宵忍泪吞。”
无依无靠的叶嘉莹展望前路,如雾里观河,模糊不定,却从未心灰意冷,她绝不向命运低头。
叶嘉莹带着女儿,睡在亲戚家的走廊,她白天抱着孩子到树下徘徊,怕吵到人家,晚上等所有人都睡了,她才能在走廊地板上铺上毯子休息。
叶嘉莹与女儿
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,叶嘉莹只能硬撑着,终于在次年,她的父亲到了中国台湾,她找到一份在台南私立光华女中教书的工作,才带着女儿换了一个生活环境,搬去父亲所在的台南临时宿舍。
住处依然逼仄,但叶嘉莹从不抱怨生活的苦。
“我真正是把什么都放弃了,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。一个人千辛万苦,历经了多少精神上、物质上的苦难,人只能是活下来就是了,除了活下来以外的事什么都不用说了。”
她白天在中学教书维持生计,晚上就回到家在过道里用煤油炉做饭。
叶嘉莹的外甥后来说,不知道舅妈这么有学问,这么厉害,因为每次去她家,都看到她在厨房做家务,以为她只是洗衣做饭的普通妇人。